
图片来源《杭州(周刊)》2018年47期
李叔同何许人也?弘一法师何许人也?很多人对此都是茫然不知。但说起先生那首《送别》,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听!听!那缥缈的歌声又从远方传来,又在耳畔响起。酒壶已空,余欢将尽,惟剩苍凉别梦,其中还残留下多少回忆的温馨?该上路的终归要上路,该告别的终归要告别。人生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夜行,惟独智慧才是我们心中的长明灯,所以要觉悟,所以要修智慧。极少数人修持了慧业,经历这段夜行之后,便能抵达光明的彼岸。李叔同先生无疑便是这极少数成就者中的一个: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这是先生辞世前在致生平至友夏丏尊、弟子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附录的四句诗偈。前两句是警劝他们勿要执迷于人生表象,后两句是对自己灵魂得到美好归宿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怀留给今天的人们的,依然是至为深切的感动。
弘一法师李叔同,俗家姓李,幼名成蹊,字息霜,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出家之前三十九年,以傲世之才浪迹江湖。先生不仅精诣诗、词、文、画,还能演剧弹琴,金、石、书法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纳罕,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和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居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太多的“想不到”拼贴在一起,仍旧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真实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弘一法师,他随时都可能穿着芒鞋从天梯上下来,让我们一睹想象中所不曾有过的另一番风采。读了他的新诗新词,我们笑了,他却不笑;我们忧伤了,他却不忧伤;我们等着他说话,他却悄悄地转过身,背影融入霞光,飘然而去,无迹可寻。
素心人夏丏尊对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于造化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神韵———是真公子自翩翩、真名士自风流、真高僧自庄重。
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这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廔、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才华出众。
辛丑年(1901),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做国文教授,用意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1905 年,李叔同决意告别故里,留学东瀛。他特意赋就一阙《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消磨:
披发佯狂走。
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
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
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
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凄风眠不得,度众生那惜心肝剖?
是祖国,忍孤负!
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
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
可有男儿奋袂来?
同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而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祖国徐、淮地区受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叹不绝。
东京美术学校为五年学制,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 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感到异常欢喜。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参与了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 年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就范。美学家朱光潜曾称赞李叔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此语赞得十分到位。李叔同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其弟子吴梦非曾回忆道:“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人家,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那样的真朋友,日子应该不会过得太郁闷。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
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
戏剧家欧阳予倩曾领教过李叔同的认真守信,在他笔下,李叔同惜时如金: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原因,竟是由于夏丏尊无意间所说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李叔同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的文章,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佛心大增。实际上,李叔同体弱多病,自认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由。而且,远离浊世,寻找净土,这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恰相吻合。
然而,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而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福基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夺。民国七年(1918)农历正月十五日,李叔同皈依三宝,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了外界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的猜测是“(他)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干什么不好?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缺少宗教情怀的人总归这样看不明白,何况是纯粹诗人性情的柳亚子。柳亚子深深惋惜这位大才子过早收卷了风流倜傥的怀抱,使中国文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殊不知,作为智者,追寻灵魂和生命的深层意义自是高于一切之上。柳亚子迷恋红尘,终未参透此中的玄奥,也就不奇怪了。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触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青岛湛山寺,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有地方好搁。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从不轻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以免自己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曾赠给他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睹,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普通僧人可及?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胸怀历历可见。他岁晚驻锡闽南,为期十四年之久,弘法的地点主要在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李铁拐的居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弘一法师弘扬律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蕙风朗月煦日酥雨,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做了明确的安排,其弟子传贯有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 年10 月10 日,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逃脱人生苦难的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三日后示寂。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堪称为佛门一代龙象的弘一法师究竟开解了多少沉溺在迷流中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吧。他涅槃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迟迟不肯飞向天国,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人世,为苦苦挣扎在火坑中的众生默默祈福。
人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宴会,先生终于回到自己心灵的净土。由大师偈语中体悟到从李叔同到弘一,这其中的纠葛,是一段生命历程的自觉与自省。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以慈悲喜舍悲悯渡世,护生护国。而圆寂前最后四字“悲欣交集”犹如他一生深邃高洁的总结。最后,把李叔同先生的人生箴言送给各位朋友:
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
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
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
以慎重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
只是,芳草依旧碧连天,长亭古道今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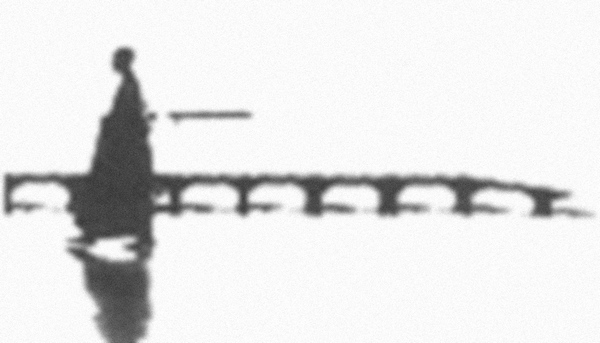
来源:《国学》2011年06期 雅妮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