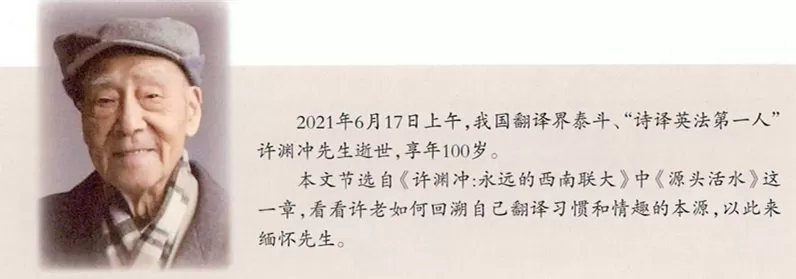
翻译的乐趣
小时候听到过的话,后来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了。九十三岁时,我在七十二行中的一行,居然得到了一项国际大奖,也可以算是中了一次状元吧。这个状元怎么中的?回忆一下过去的酸甜苦辣,现在会觉得比当年更苦还是更甜呢?一般说来,痛苦已成过去,多半都会淡忘,有的甚至还会变成乐趣。
1936年我十五岁,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读高中一年级,那时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北,正在进犯华北地区。为了准备抗日战争,江西全省高中一年级男学生都集中在西山万寿宫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在烈日下全副武装操练,没有自由,夜里还要起来站岗,睡眠不足,苦不堪言。西山风景虽好,但当时填了半首词,发出的却多是怨言:
南昌故园,西山古庙,
钟鼓惊梦,号角破晓。
参天松柏,垂地杨柳,
万木浴风竞自由,
望长空,
恨身无双翼,难追飞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一同接受军训的同学后来多有成就,谈起当年事来,却觉得几乎可以和西山比美了:没有当年的钟鼓惊梦、号角破晓,哪能保住今天的参天松柏和垂地杨柳呢!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到远方,又可以看到近来,近来的喜就可以减少过去的苦了。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可以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例如1938年至1939年,我和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同上大学一年级的英文课,叶公超教授讲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时,课文中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并不表示被动的意思,全班同学都没有发现,只有杨振宁一个人提出问题。当时大家只觉得杨振宁好学爱提问而已,不过小事一桩。等到1957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我才想到这是他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结果。1957年以前,物理学家都认为宇称是守恒的,他却能注意到不守恒的现象,结果得了大奖。当年他发现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的用法,不就已经显示了善于发现异常现象的才能吗?这就是回忆可以起放大镜作用的一个例子。
七十二行之中,有一行是翻译。什么是翻译?有一个西方语言学家说:翻译就是两种语言文字的统一。如何统一呢?把一个国家的语言转换成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就是统一。在西方国家之间,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英、法、德、意、西等国的语文,约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找到对等词,所以翻译比较容易。但是在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之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也是据电子计算机统计,中西之间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可以找到对等词。那不对等的一大半怎么办呢?不是表达得不如原文,就是优于原文。因此中西互译的时候,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找得到对等词,那并不是不可以用;如找不到,那就要尽可能选用优于原文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之间的翻译基本上可以用对等译论,而中西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就要用优化译论,甚至是创译论了。
1939年至1940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二年级。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西南联大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因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占领了北京(当时叫北平)和天津,三校奉命南迁长沙,后又西迁昆明,组成联大。当时清华师生约占全校一半,北大约占四成,南开约占一成。1938年迁到昆明后,教学楼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的校舍,宿舍租用昆华中学南院、北院。
我大学一年级住昆华中学北院22室。杨振宁和他父亲杨武之教授一家住北院附近的文化巷11号,钱钟书教授也住在那里。就是在这一年,我见到了这两个重要的联大人。
我二年级住昆华中学南院3室,就是在这间小房子里,我读到了柯尔律治的名言“散文是编排得最好的文字,诗是编排得最好的绝妙好辞”和英国《泰晤士报》登载的“面对硝烟”和“涂脂抹粉”的新闻。后来翻译《为女民兵题照》时,就用从报纸上学来的表达方式来翻译“红装”和“武装”了。后来我又把译文改成:They love to be battle-dressed, and not rosy-gowned。这样从字面上看更忠实于原文,而且原诗第二行的“演兵场”译成drilling ground,和“武装”(rosy-gowned)正好押韵,并且和原诗更加音似,所以后来出版时,我就改用这个意似而且音似的译文了。毛泽东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再版时,我认为意似不如意美重要,音似更不如音美和形美受欢迎,于是恢复了原译。原译出版之后,英国一家杂志编辑来信,认为译文极妙,甚至可以说是胜过原文。

父亲“礼”或“善”的教育
这种情趣是从哪里来的呢?仔细回想一下,追本求源,才发现源头活水还是我父亲爱好整洁的生活方式。他教我从小就要将文房四宝放在最方便取用的地方。后来我写字的时候,把文房四宝扩大到文字,也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最方便取用的地方也可以概括为最好的位置。于是“面对硝烟”和“涂脂抹粉”这两个四字成语就放到女民兵身上去了。这样日积月累,哪怕一天只碰到一个,如果能够放在最恰当的地方,一年就有三百,十年就有三千,有这么多得意之笔,那还能不中状元吗?
父亲培养了我把最好的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的习惯,但他不只是在生活上这样要求自己、要求子女。而在工作上呢,我记得他最早的工作是在江西抚州(今天的临川)第七中学管理财务。七中出了一个名师,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游国恩,一个更有名的学生饶漱石(他和陈毅同是华东军区领导)。父亲管理财务很出色,得到七中领导信任,我就又把他管理钱财的条理应用到翻译上来了。
父亲培养了我对秩序的爱好。据冯友兰说,我国古代“礼乐之治”的“礼”就是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就是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如果说“礼”是“善”的外化,那么,“乐”就是“美”的外化。父亲教我要爱秩序,这是“礼”的教育。母亲生前爱好图画,给我的是对“美”的爱好,这就是“乐”的教育。

母亲“美”或“乐”的教育
父亲用行动对我进行了“礼”或“善”的教育。母亲对“美”或“乐”的爱好又是怎样影响了我的呢?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母亲却是一百年前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但是母亲去世太早,她教我认“字角”的事是父亲告诉我的。“字角”是一张小方块纸,正面是一个字,反面有图画。小时候母亲就是这样教我看图认字的。我仿佛有个印象:我抱住她的腿要她教我认字,她忙,没有时间,我就用头顶她的肚子,那时她正怀孕,却对父亲说:“让他顶下来也好。”因为她梦见一个女鬼向她索命。生下妹妹之后,她果然离开了人世。妹妹没人喂奶,也被送人做童养媳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周岁,只记得她留下的遗物中,有两本图画、一本作文。图画中的花木鸟兽对我的吸引力不大,却引起了我对“美”的爱好。作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项羽与拿坡仑》(拿坡仑,现多译作“拿破仑”),后来我十岁时读《秦汉演义》,读到少年英雄项羽大破秦兵的故事,不禁手舞足蹈,非常崇拜。再读到垓下之战、霸王别姬,对失败的英雄充满了同情。这是不是开始培养了我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
后来听京剧唱片,听到金少山唱的《该下歌》,声音洪亮,简直像是霸王再世,使我知道了音美和意美的关系。我把项羽的《该下歌》译成英文,原词只有四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驰)。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第一句“力拔山兮”很形象化,但太夸张,如果按照字面译成I am powerful to pull up mountains,读者恐怕无法理解。“气盖世”的“气”字没有对等的英文词,勉强解释为英雄气概吧。“盖世”从正面说是超过全世界的人,从反面说是全世界无人能及,能不能译成With heroism unsurpassed?我觉得如果要求对等,恐怕很难译得像诗,只有按照中国学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论来翻译。“从心所欲”是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不逾矩”是不超过客观规律所允许的范围,不违反原文的意思。于是我先把译文改成:I could pull mountains down, oh!with might and main(“气盖世”说成“用尽全力”)。第二句“时不利兮骓不逝(驰)”按照字面可以译成:Time is unfavorable, oh!my horse won't run(gallop)。原文“逝”在当时可以和“驰”互用,如果说是奔驰,那么为什么战马要奔驰呢?还不是为了作战吗?所以如果要选择更好的表达方式,第二句可以改译为:But my good fortune wanes, oh!my steed won't fight。
母亲影响了我译诗的“音美”,父亲则影响了我译诗的“形美”。
来源:《阅读》2021年第72期 许渊冲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