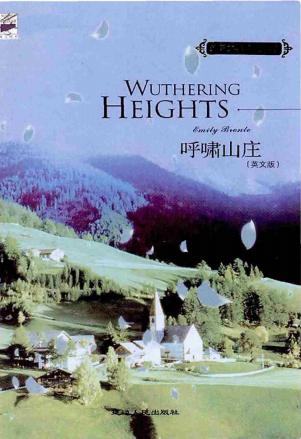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问世时,因其凌厉风格与维多莉亚时代的文学趣味不合,遭到评论界严厉贬抑。以至于夏洛蒂为小说写序时,不得不以妹妹艾米莉终日穿行在石楠丛中的环境局限为其做无奈的辩解。但到了20世纪,《呼啸山庄》的声望日高,受到研究者的特别重视。
关于《呼啸山庄》的研究角度很多,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小说魅力的主要来源还是其爱情主题,爱与恨的强力纠缠与撕扯。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评:“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
爱情“理型”:契合与执着
小说中,艺术想象力突破了作者枯燥闭塞的生活(艾米莉没有恋爱经历),创造了希克厉与卡瑟琳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洛克乌恶梦中看到窗外卡瑟琳的幽灵,在卡瑟琳临终前两人不顾一切地拥吻、流泪和吵骂,希克厉试图掘开卡瑟琳的坟墓,尤其是小说结尾卡瑟琳和希克厉的鬼魂在荒野上相拥游荡,这些都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
爱与死是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呼啸山庄》里的爱情,是绝无仅有的。循着惯常思路去发现卡瑟琳和希克厉的爱情基础,难寻踪迹:没有社会理想的同步,没有共同的事业经营,没有奉献或感恩,没有诚实的信托,没有睿智机敏的言辞吸引,甚至没有体貌欣羡(卡瑟琳说,“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模样长得俊俏”)。人格和精神层面的认可也被虚化了,没有价值观考验,没有思想高位的征服或交流互动(他们从未讨论过人生或社会),没有心灵碰撞的火花(像《少年维特之烦恼》绿蒂情不自禁说出“克洛卜史托克”)。唯一的理由就如卡瑟琳所说:“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他跟我是同一个料子。”
小说中写到希克厉和卡瑟琳作为“同一料子”的行为,是他们共同反叛专制家长亨德莱对希克厉的镇压,“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两人一块儿一清早就奔到荒原上去玩一整天,至于事后的惩罚变得无非是让他们好笑的事儿罢了。……只消两个人到了一块儿,他们便立刻把什么都忘了”。这当然可视为一种认同,但此类少年游戏,筑成终其一生的爱情基础,说来还是过于简单了。其实艾米莉式的爱情并不着意理解和考验的过程,她在《呼啸山庄》中为希克厉和卡瑟琳所构想的爱情基础,是二人性格与精神的天然契合,是一种类似于柏拉图哲学那种高度抽象和先验的“理型”(或译为“理式”),只可能以具体内容对其填充,但无法以具体内容对其更改。
小说第十七章,卡瑟琳下葬当天,借着希克厉离开呼啸山庄去画眉田庄远远跟随卡瑟琳最后一程的机会,被希克厉当成报复对象虐待的伊莎蓓拉逃回到画眉田庄,她完全认清了希克厉的恶魔面目,更加惊诧卡瑟琳对希克厉的爱有多么的不可理喻:“卡瑟琳的口味也真是与众不同,把他看得这样透,还对他爱得这么深。”伊莎蓓拉一语中的:不管希克厉变成什么,甚至在希克厉已经变成报复的恶魔后,卡瑟琳不但没有因他对自己家(娘家和婆家)人的凶残行径而对他的爱情有丝毫减损,反而爱得变本加厉,不顾丈夫反对,以死相拼也要见到希克厉。卡瑟琳对希克厉的爱是永远定格在某一点上了的,到了执着到死不肯悔改的程度。
希克厉同样是爱得执着。小说第三章,洛克乌恶梦惊醒希克厉,希克厉登上窗台,流着泪面向窗外寒风呼啸的荒野呼唤卡瑟琳的幽灵:“进来吧!进来吧!卡茜,快来吧。啊,你再来这一回吧!啊,我的好心肝儿!这一回你就听了我吧!卡瑟琳,至少听我一回吧!”洛克乌感叹:“那一堆疯话里头,挟着那么一股强烈的痛苦、辛酸,使我只感到同情,再不觉得这疯癫有多么可笑。”
洛克乌感动于希克厉疯狂的理由,是他对死去20年的一个人爱情不减,超越了尘世,而与永恒相联。因为,在现世中,哪怕相离千万里,也还有相见的预期,但死去的人,只能是爱的符号。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说:“爱情的问题都是在床上解决的。”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爱情观不同,《呼啸山庄》完全背离了这一定律,希克厉与卡瑟琳的爱虽已达到超越生命程度,但与生理快感无关,与欲望吸引无关。小说中不但未做片言之语的床第描写,甚至对男女主人公的相貌也根本未着意突出其性别特征。即使卡瑟琳临死前二人最后一次相聚,生离死别的疯狂,也有纳莉在场,两人只是拥抱,亲吻。
因为欲望缺席,两性吸引无效,也就彻底断掉了对象的替代可能。伊莎蓓拉也是美女,而且比卡瑟琳肤白,金发,但却只能成为希克厉凶残报复的工具,而根本不是欲望的对象。所以,希克厉的爱,甚至都不能说是朝向女人的,而只是朝向精神的。欲望对象可以替代,而精神契合对象唯一,不可替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与波德莱尔那首《恋人之死》的爱情哲学相映照:“两颗心好比两堆烈焰/ 两个灵魂合成一对明镜/ 在互映中闪现光辉。”
爱情与婚姻:卡瑟琳的生命之痛
小说第三章,洛克乌被风雪阻隔在呼啸山庄,恶梦中听到卡瑟琳在窗外哭诉:“二十年啦。我已经作了二十年的流浪人啦!”英国作家福克斯评:“这是整个英国文学中最为令人激动的一页。”
所谓“令人激动”指的是卡瑟琳死后20年的灵魂流浪。其实这一灵魂流浪的宿命,卡瑟琳生前已预知了,因为她嫁给埃德加·林敦,背离了她对希克厉的爱,在现实的婚姻和理想的爱情之间,撕裂了自己。
第九章,埃德加向卡瑟琳求婚后,卡瑟琳向纳莉倾诉苦恼,纳莉说:“你可以脱离一个乌七八糟、没有乐趣的家,来到一个富裕体面的家庭里;你爱埃德加,埃德加也爱你。一切似乎都很美满称心呀,阻碍又在哪里呢?”
纳莉作为一个类似于全知的叙事者(在场景和时空叙事上不是全知,但价值观上纳莉是担当全知判断的),这算是明知故问。当卡瑟琳考虑到现实生活的可能而对爱情舍弃的同时,她也完成了对自己人格的撕裂。对此她自己甚至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面对纳莉的追问,她一只手拍着自己的额头,一只手拍着胸房回答说:“在这儿,还有这儿!……总之,在那灵魂居住的地方。在我的灵魂、在我的心坎里,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做错了。”
放弃一个穷小子,选择一桩体面的婚姻,谁也不能说这是不明智的,但卡瑟琳却一边作出婚姻决定,一边恐惧未来的痛苦:“天堂不像是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人世来,惹得天使们大怒,把我摔了下来,直掉在荒原的中心、呼啸山庄的高顶上,我就在那儿快乐得哭醒了。……不说别的了,这就足以解释我的心事了。我嫁给埃德加·林敦,就像我在天堂里那么不相称。”“他(希克厉)跟我是同一个料子,而林敦呢,却就像月光和电光、冰霜和火焰那样和我们截然不同。”
但卡瑟琳欺骗自己,为自己找到结婚的理由:“要是我跟希克厉做了夫妻,我们两个只好去讨饭吗?要是我嫁给了林敦,那我就可以帮助希克厉抬起头来,安排他从此再不受我哥哥的欺压。”其实她知道这个幻梦从一开始就破灭了,死之前她挣扎着表达自己的悔意:“我给人硬是拖了走,撇下了山庄,断绝了我童年时代所有的联系,尤其是我那时候的一切的一切——希克厉,而一下子成了林敦太太、画眉田庄的主妇、一个陌生人的妻子,从此我就成了我当初小天地里的流亡者、门外汉……我准知道只要让我重又回到那边长满石楠的小山头上,那我就会恢复我本来的样子。”
而卡瑟琳想重回呼啸山庄,只可能是在洛克乌梦中那个情境了。
为爱一个人可以毁掉世界:绝世恶魔希克厉
卡瑟琳临死前二人最后见面时,希克厉指责卡瑟琳:“为什么你要看不起我?为什么你要欺骗你自己的良心,卡茜?……你曾经爱过我;那你有什么权利丢开我呀?”在希克厉的逻辑中,卡瑟琳丢下他而嫁埃德加·林敦,成了他向两个家族疯狂复仇的理由。
卡瑟琳从画眉田庄回来后,穿着举止为之一变,由野丫头变成了上流社会的小姐,希克厉被冷落,纳莉安慰他:“谁知道你的爸爸不是中国的皇帝,你的妈妈不是印度的女王呢?他们每个人一星期的收入,就可以把呼啸山庄连同画眉田庄一起买下来啊。”纳莉安慰的话语:变成有钱有势的人,成了后来希克厉的人生追求,他归来后,就循着这个轨道进行着他的复仇,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与亨德莱赌博,从亨德莱手中嬴得了呼啸山庄,诱骗伊莎蓓拉私奔,甚至利用自己的儿子小林敦与小卡茜结婚来占有画眉田庄的财产。他用复仇来补偿自己失去爱情的痛苦,人性完全扭曲。结果他却并没有在复仇中获得意义,就如小卡茜所说:“没有人爱你,……你很悲惨,不是吗?像魔鬼一般孤独,又像魔鬼一般嫉妒。没有人爱你——等你死的时候,也没有人会为你哭!”
被虐待的新娘伊莎蓓拉是最有资格评论恶魔希克厉的。第十七章,伊莎蓓拉逃回后说:“他真有办法,把我的爱情完全窒灭了,……就算他喜欢我,他魔鬼般的脾气还是要暴露出来的。”其实希克厉清楚自己就是一个魔鬼:“我不懂得怜悯!我不懂得怜悯!虫子越是扭动,我越是恨不得挤出它们的肠子来!这好比是一次出牙,我精神上越是感到痛,我越是使劲地磨。”
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史文朋对《呼啸山庄》有一段特异的评论:“笼罩全书的气氛是那么崇高,那么健康,以致……可怖景象在这里几乎被一种高尚纯洁和激昂率直的总印象所中和了。”问题是,什么是小说中的“高尚纯洁”?只能是希克厉那种疯狂的“爱”。希克厉甚至认为他的报复并不过分,跟他失去的还不能比,他向卡瑟琳报怨:“既然你把我的皇宫铲成了平地,不要搭一间茅草棚,赏给我算是家,还得意地夸耀自己良心真好。”在小说情节主体上看,希克厉是被否定的形象,但他又是小说魅力的主要来源。他是制造仇恨和冷酷的专制暴君,同时在“爱”这方面,他又是最富于力感的。他病态性格的核心,是把卡瑟琳、把爱情当作全部世界、全部的生活意义。
为了所爱的一个人,他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在小说的审美结构中,他是十足的恶魔,而他的爱又十分感人,这是个悖论。但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现实尺度有着不可简单对等替换规律的话,就必须看到,不管爱情的理由有多么动人多么充分,希克厉式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可原谅的;希克厉式人格,不仅对所爱的人,对世界,都是可怕的祸害根源。
爱之永恒:荒野游魂
小说结尾,一个牧羊童看见卡瑟琳和希克厉的鬼魂在荒野上游荡。不细心的读者在读到希克厉死去,小卡茜和哈里顿一对年轻人要缔结美满婚姻的情节之后,可能忽略这里的一两句交待。但这绝非小说随意安排的一个情节,它对全书的回照,远比小卡茜和哈里顿结婚的光明前景要重要得多。
这一结局,在小说的叙事中,早就多次暗示过。第五章,呼啸山庄的老主人老欧肖死了,希克厉和卡瑟琳非常悲痛,大哭,回到房间,纳莉半夜过去看,他们俩在互相安慰,“那两个小东西在互相安慰着,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好。世上再没哪个牧师能像他们的天真烂漫的谈话那样把天堂描绘得那么美了。”但后来的情节证明了,希克厉和卡瑟琳不属于宗教的天堂,他们只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天堂。
卡瑟琳临死前见希克厉时说:“让我最讨厌的东西,说到底,就是这一个支离破碎的牢笼。我给关禁在这儿已经关腻啦。我盼望得不耐烦了,要逃到那极乐世界去,从此永远在那儿了。”但卡瑟琳死了20年,她也未能达到她所说的“极乐世界”,她的灵魂无所依归。这种局面,到希克厉死后才改观了,两个人相拥着在荒野上游荡。
第三章,洛克乌恶梦中见到卡瑟琳的幽魂,希克厉进屋,咒骂洛克乌:“我但愿你下××去。”译者方平加了个注:当为“下地狱去,当时书本上遇到渎神或粗野的话故意删去,以适应上流社会的语言习惯”。可知,当时“地狱”和“天堂”这类宗教意识是十分牢固的。在宗教意识浓厚的英国文化背景下,小说让死去的人灵魂既不去天堂,也不去地狱,而是在荒野上游荡,这是不可思议的。这表明,他们是被主流文化所放逐的,也甘愿自我放逐的。
纳莉在卡瑟琳灵前想到:“那无边无际、照彻光明的境界一定会在身后来到——他们进入了‘永恒’——在那儿,生命之火永不熄灭,爱的应和无休无止,到处充满了欢乐;”纳莉说的永恒,是双关的,明指宗教天堂,其实是说卡瑟琳的真正归宿,因为卡瑟琳在死后并未能获得宁静,是希克厉死后,她与希克厉二人并走于荒野上时,才是他们爱情的归宿。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西方文化传统早就有超越生命的永恒追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论到过永恒之爱时说,人见到美的身体,推而至于身体之美,再往上到灵魂之美,……最后抵达“美”的本身。它是“永恒长存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也说:“只要有可能,我们应努力探知永生不朽的事物。”在筑就了西方思想史思维框架的两位古希腊先哲那里,探求超越有生之外的永恒的追求,是后来欧洲基督教兴起的古代思想潜在先源。但《呼啸山庄》的永恒爱情,却是与基督教信仰构成某种背反的,这也是小说当时被严厉贬抑的主要原因。稍有宗教意识的人,都能从小说结尾处希克厉和卡瑟琳相拥游荡于荒野的情节,读出背离基督教思想的意思——他们既不去天堂,也不下地狱,自己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在那里寻得其爱情自由。
在合法的、世俗的结构里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这个世界,是相爱的两人共同构筑的,既非天堂,亦非地狱,超越了西方宗教价值体系。荒野游魂,是《呼啸山庄》的爱情乌托邦,从而使小说的爱情找到了永恒的安身之所。
来源:《社会观察》2015年06期 姜书良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