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因为有颜色而美,而中国的文字皆是有颜色的。喜欢中国的文字,喜欢中国的文字写成的诗篇,更喜欢写诗的诗人,他们是人间最美的颜色,倾城倾国。
紫,是形声字,形声字总没有多少意思,但因为止的起源是脚趾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看着像是一个人脚踩着丝用刀一点点割,一个字竟就可以成一幅画。
与谢芜村有俳句云:“春阑珊,淡紫透霞残,筑羽山”,说的是那筑羽山的春景里,淡淡的紫,薄得如纱透出了霞色。天下,用紫用得最好的只有上帝。所以看紫要跃过人间的物事,看天看地。
纯纯的紫就是紫气东来的紫,是老子过函谷关之前,让关尹喜见到的那从东而来的紫。浅一些的紫有紫罗兰,是紫色的30岁,再浅一些就是“雪青”,是紫色的20岁,最浅的浅到梦里,就是紫丁香的颜色,正好是十六岁的花季。
紫是法国的普罗旺斯,那是个被熏衣草熏紫了的地方。所以有位畅销作家,想要逃到普罗旺斯的紫里做一只可以睡在上面的甲壳虫:“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旺斯做个时间的盗贼。”而那些在这里种植熏衣草的人们,是天堂的园丁。
一个满目皆紫的梦幻般的地方,中国也曾经有过,春秋时代,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于是一国尽服紫,想象那种场面,天地之下,唯有紫色最猖狂,每个人似乎都是一朵熏衣草。
紫色的花除了熏衣草的紫外,还有那开在林徽因前的紫藤花的紫。那紫开放了,可是却只是一味的安静,安静得只让林徽因这样的女子看见:
紫藤花开了,
轻轻的放着香,
没有人知道。
楼不管,
曲廊不做声,
蓝天里白云行去,
池子一脉静;
水面散着浮萍,
水底下挂着倒影。
蓝天里白云行去,
小院,
无意中我走到花前。
轻香, 风吹过
花心,
风吹过我,
望着无语,
紫色点。
林徽因的紫是雅的,是水上的浮萍,是水底的倒影,是落到诗人手上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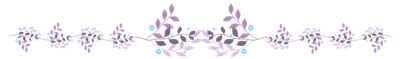
而张爱玲的紫,是落到苍生上的那暗花,风生水起只为活着的那点颜色。所以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张爱玲也曾表白自己不属于冰心、白薇一派。她的作品没有女性作家的温婉、柔媚,无论是银紫或是青灰总之只是苍凉。
紫色的花还有开在川端康成《古都》里的紫花地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它:“其叶似柳而微细,夏开紫花结角,平地生者起茎,沟壑边生者起蔓。”然而,在《古都》的少女千重子面前,紫花地丁寄生在枫树树干上的两个小洞里,两株远远地隔着——约莫隔了一尺。所以千重子会想:“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所以川端康成写了《古都》给了她这个答案。
而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提到一种紫草,可以做药也可以染色,他说:“如今之紫草, 未花时采。”短短几个字,这花要开未开间就有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风光。
那年,当白话文开始提倡的时候,随着它一起流行着紫色墨水写的字,丰子恺说:“紫色为红蓝两色合成。三原色既不具足,而性又刺激,宜其不堪常用。但这正是提倡白话文的初期,紫色是一种蓬勃的象征,并非偶然的。”
所以,丰子恺也常常“买三五个铜板洋青莲,可泡一大瓶紫水,随时注入墨匣,有好久可用。我也用过一会,觉得这固然比磨墨简便。但我用了不久就不用,我嫌它颜色不好,看久了令人厌倦”。
令人厌倦的是紫色的字,而无法让人厌倦的是紫色的花瓣,比红色要静雅;是紫色的烟,比青烟要贵气;还有紫色的天空,那渐深渐紫的薄暮的天空,就那么一闪,闪出几缕紫光来,世界就沉静了。
所以,紫色不能太多,多到铺满整篇丰子恺的文章,要的只是花瓣里、云烟里和天空上那惊鸿一瞥的刹那,刚刚好。所以,紫是暮色,是天闭眼前眼里流露的最后一丝余光。康定斯基说:紫色是冷红经过蓝色向后退,表现熄灭。是太阳的光,经过浅蓝深蓝暗蓝的天空,渐渐灭下去。一种意犹未尽的深远。
所以,紫像是先秦,宴席未散,花朵还未睡去,淡淡的倦,倦看苍生。就像一朵花微微地颓废,却依然开得好美。每一种美都独一无二,都开天辟地。
那时候,《诗经》里的每一个月,都还像诗一样的美,清淡的美。他们的五月斯螽动股,他们的六月莎鸡振羽,他们的七月正是食瓜,八月却是断壶的时候……
此时,英雄还在擦剑,美人还在采着最后一朵卷耳。而男人爬到田埂上,跺跺脚泥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行人也路过今天要走的最后一条小河,放脚到水里,开心地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而百里奚的妻还挡道弹琴而唱夫君——你发达了,为什么还不来接我:“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别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一心一意地认定和坚持,于是也成了诗人。
而管子突然警觉,对听众说:“墙有耳。伏寇在侧。”众人屏息,倾听黑夜来临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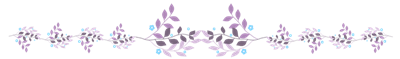
屈原挟一朵兰而来,江边暮色正好,兰花还开在紫茎上,屈原叹一声自己:“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说他的清明如兰紫茎般贵气。
有渔翁来问:你不是屈原么?怎么会到这里?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又问:“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而自令见放为?”屈原说:“宁赴湘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屈原,一个如兰紫茎般的人,是《诗经》里的那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君子,可是当他成为温润如玉的君子后,天地之间,已经没有他能自处的地盘。所以,他只能落到水底,那里才有他要的清明。
他一生,只有忠诚,而他一生,却没有人相信他的忠诚。所以,他要写《离骚》,但那时他以为天地总有他一席的生存之地,所以他做的是那出世而未离世的蝉:“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他以为自己可以依附着一棵树而浮游于尘埃之外,他既可以做兰也可以做人。他要的是两全。
后来,最有煽动力的张仪来了,带着秦国的使命和谎言,如一只阴险的雕来到了楚楚可怜的楚国,他找寻着他可以下手的破绽。对于一个不相信屈原真话的君王来讲,张仪要下手很容易,只要是谎言,楚王就能相信。所以他编造了一个最大的近乎于无赖的笑话,让楚国跟齐国断交,说秦国愿意献出六百里土地。怀王贪心,果然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并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对使者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过有什么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大规模起兵攻打秦国。于是好一场混战,打得风起云涌,可没有盟国相助,楚国打得很辛苦。
第二年,秦国提出割让汉中一带土地和楚国讲和,但楚怀王说:我不希望得到土地,只想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说:“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到了楚国,又是一番花言巧语,说通了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放了张仪。等屈原出差回来,问怀王:“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已经来不及。所以,后人想起楚怀王的时候,也只是笑他:宫花一朵掌中开,缓急翻为敌国媒。六里江山天下笑,张仪容易去还来。
后来秦昭王与楚联姻,想与怀王见面。怀王打算去,屈原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但怀王稚子子兰劝怀王:为什么要拒绝秦王的好意?于是怀王去了,被秦扣押,以求割地。最后辗转,怀王终死于秦而归葬。
又后来,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国的人都指责子兰劝怀王入秦。而屈原,虽流放,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所以在文章里提起了这件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又派人去顷襄王面前中伤屈原,顷襄王怒而放逐了屈原。
此刻,屈原才知道,自己并不是蝉,是至清的水,而无鱼,也不容忍有鱼。于是屈原披头散发、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走在江边,招魂,招的是自己的魂,唱的还是那紫茎上的兰:“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屈原唱的那些诗,是紫茎上的兰,而屈原,恰是那兰下的紫茎,梗直地顶着,顶着一朵朵兰花开。屈原终究发现,他在人间做不了兰,那么他可以做那兰下的紫茎,将他的理想与希望化做文字,变做朵朵兰花,让众人见着做兰的态度,和做人的气节。屈原死后,天地昏暗,紫色斑斓的人间即将进入大秦那万色归一的夜里。蛰伏着,等着那大汉黎明的蓝光到来。
若说屈原是深厚而不容许有一丝淡色婉转的黛紫色,那么他的学生宋玉,就是紫丁香的颜色了,浅浅的紫色,有屈原的文采,却更有自己做色的婉转。他懂得妥协,所以就淡成了丁香。他写的东西,总是让君王喜欢。他说的话,也总是投君王的喜好。所以他一生无事,得以善终,不起微澜到无人记得他去世的年份。只知道,他去世之前,大约还听说了荆轲去刺秦的事。他的生,也无人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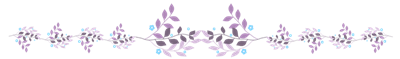
大家只知道,屈原投江后,就出了一个宋玉。陪伴在君王之侧,写得一手好文章。那君王,因为他的文章,竟然也因此而成了文化的主角——在人间,君王给诗人生存空间,而在文章里,只有诗人才是君王。而在这传了几千年的文章里,人们依然还能知道,宋玉其实是个美男。他的美,美到都招惹登徒子这样的人嫉妒,说他:“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楚襄王去问宋玉。宋玉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他说得精妙,最后,好色的冠名反而落到了登徒子头上。他也说得好得意,所以,把文章写下来,从此让人们知道他自己如何的貌美。
伴在君侧,因为在做人的颜色上的妥协,所以倒也因此留下了不少曼妙的文章。比如跟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楚襄王乃披襟而挡之,一时的得意问:“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这回答只是媚。
后面的话,却风起云涌地畅快:“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原来雄风当是起于那微小的青苹之末,而后盛怒于土囊之口,再然后抵花叶而振气,最后落到玉堂之上,他说的是大王,其实夸的还是他自己。
他说话太精明,也惹人喜欢。而他的一生,嘴里是一个宋玉,心里是另一个宋玉,所以诗人得以存活。因为宋玉做人妥协,所以得以活着写诗,而屈原不能妥协,所以不能活着写诗……宋玉的颜色,是在紫色里看着时机调了一些白,一些红,一些青,调得正好,所以,成了丁香色。
他去世之前,荆轲已经在易水边唱完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英雄没有回来,而秦终于大并天下。夜色降临,所有的颜色重新渲染,等着新的篇章掀起。有夜行人穿着黑衣,不,应该是紫衣,夜里的黑衣反而让人看得见一团黑影,所以他们穿着接近夜空颜色的深紫色夜行衣,潜行。整个夜里,风生水起,渐至风起云涌,那些擦剑的英雄,将剑放回了剑匣,背剑潜行,杀入了阿房宫……这夜很短,短得嗖地一声,未曾让秦留下多少诗歌和诗人,天就亮了。
来源:《国学》2010年07期 倾蓝紫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