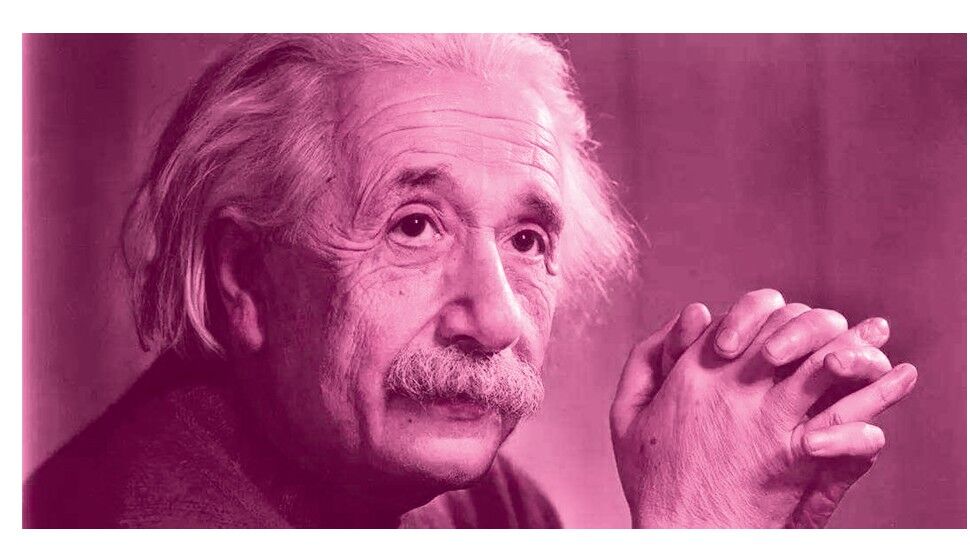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诚恳而善良的灵魂。他具备的一切品质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毕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那时他到学校来和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共同指导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学术讨论会曾经推动很多人去钻研物理学上的新课题。此后过了好多年,我们才在柏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重新见面。在那次会上,他和能斯脱、普朗克宣讲了热力学基础理论。1931年,他应德国政府资助的费城德美文化协会邀请,以德国政府代表身份初次访问美国。他到达美国时受到了德国驻洛杉矶领事的欢迎;从帕萨迪纳回国时,领事又亲自到场送行。爱因斯坦到美国不久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希特勒取代了兴登堡。爱因斯坦离开美国不到一个月,那位领事就被希特勒召回德国。
爱因斯坦到达帕萨迪纳时,我随好几个达官显贵去迎接他。那天场面很大,四周挤满了欢迎的人;儿童们手里都拿着鲜花。在市政府大礼堂前面举行欢迎仪式的过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里,就满面笑容走过来和我握手。
“啊,亲爱的卡门,”他说,“在这里见到你我真高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广场上的喷泉,那喷泉顶上有一个翻滚、弹跳着的小球。“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小球在喷泉顶上不掉下来。”
我对他说,如果小球的重量和喷水的动量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关系,一旦小球出现在喷泉顶部,就会停留在那里按水力学规律运动,它一偏离平衡位置就自动进行校正,因此始终不会掉下来。
“好极了。”他点点头,然后又回去参加欢迎仪式。
数月之后,我对爱因斯坦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的羊毛衫加一只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他要我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我在洛杉矶奥列薇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的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远近闻名,因此他在那里从未碰到过上述麻烦。我猜想,街上谁也没有认出我身旁的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蓦然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这两句他立刻就坐了下去。
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过许多次关于物质结构的学术讨论会。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一起主持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密立根、托尔曼、鲍林和爱泼斯坦,这是个多高水平的学术小组啊!我记得,爱泼斯坦的论述清澈明了。而奥本海默表达问题的方法太复杂,因此难以理解。他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式常跳过好几步,又以为听的人都能跟得上。爱因斯坦接在奥本海默后面登上讲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将尽力而为。
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耍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
我在爱因斯坦身上打过一个主意,结果却完全失败了。谢天谢地,幸亏那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情。
有个匈牙利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我发现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萨迪纳一家大餐厅里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有个心理学家还写过一本专门介绍他的书。我和妹妹对他的处境感到很惋惜,觉得他在美国需要有个显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听他的演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把南加州有名的音乐会代理人都请来赴宴。一方面让他们见见这位数学大师,另一方面聆听他拉小提琴。不用说,到时候他们纷纷赶来了。
那天晚上,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不料在这个当口,爱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下竟触怒了哈齐,他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罢就真掼纱帽不弹了。我们期望美国音乐界重视哈齐的计划就此成了泡影。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结果,所有来客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而把布达佩斯的神童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看,那位傲慢无礼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错特错了。其后几年,法国钢琴大师卡扎德絮和爱因斯坦合奏就丝毫没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贝诺·古腾堡教授也常为爱因斯坦作钢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后我问爱因斯坦,古腾堡钢琴弹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很难跟上。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地震学家弹钢琴不是也有节奏吗?”
爱因斯坦笑笑说:“他的节奏很好,但很难捉摸。”
1932年,爱因斯坦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内中详情我不大了解。不过我料定普林斯顿大学另有一位“密立根”,此人名叫亚伯拉罕·费莱克斯纳。他不仅替爱因斯坦安排了一个终身职务,还向他提供了满意的生活条件。我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经常接到他的来信。有一次他来信要我参加他发起的“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紧急行动委员会”。我对这类组织从来就不感兴趣。比较起来,我对在以色列办一所医科大学或向西班牙提供促进艺术发展奖学金倒是更为关注。我以恕不从命回复了爱因斯坦,并说:“幸好我不是原子科学家,作这种决定要简单多了。”
来源:《北方人(悦读)》2019年第12期 冯·卡门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