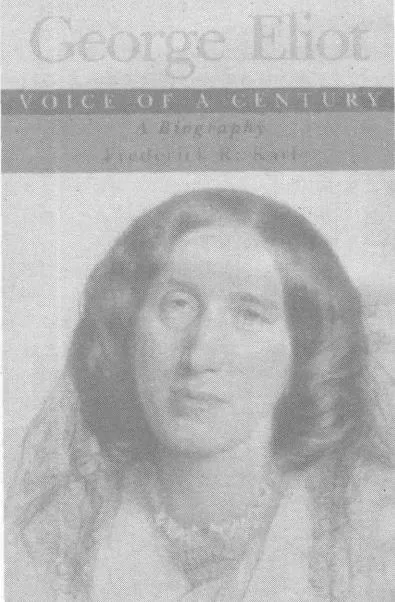
《亚当·比德》无疑为乔治·爱略特带来卓著声誉,1859年出版后好评如潮。《泰晤士报》称其为“一流小说”。众人为其“独特的男性视野”叹赏不已。《经济学家》更认为“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与女性小说的本质区别”。惟有狄更斯老辣犀利,目光如炬地辨识出作者的男性伪装。不过,这段颇有兴味的文坛逸事并不能说明19世纪的大多数评论家和读者就如何的平庸和粗疏,从纯粹的小说文本来看,这部作品颇为符合当时标准的男性小说特点,首先是其男性的叙述人身份;其次是大量哲学宗教性的思辨议论和说教,及谋篇布局、结构设置上的理性控制;再次是全篇泾渭分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理想和标准。这些恐怕都是时人断定爱略特为男性的最理所当然言之凿凿的证据。
其实,在爱略特的一生创作中,《亚当·比德》远非成熟,缺点明显。故事发生在她稔熟的英国乡村生活的背景上,一个叫海蒂的漂亮、虚荣、浅薄的女孩子被诱失身并杀婴,临上绞刑台前改判流放海外,最终在流放地死去。与她形成对照的是卫理公会女布道士黛娜,美丽圣洁,倾情宗教而博爱众生。她自始至终充当海蒂(还有其他人)的灵魂救赎者。在海蒂临刑前夜陪伴和抚慰她。然而,颇为戏谑的是,这位献身上帝的圣女却在故事结尾与曾挚爱海蒂的男主人公亚当·贝德成婚,小说在儿女绕膝、天伦之乐般幸福家庭的氤氲气氛中结束。这画蛇添足的一章历来为后人所诟病,爱略特却坚持己见,其中自有深意存焉。
熟悉西方文学和文化史的人,对这个故事的寓言性构架不会陌生。海蒂和黛娜无疑是古希腊赫拉克勒斯笔下的卡吉亚和阿雷特的维多利亚版。圣女与荡妇、灵魂与肉体、救赎与犯罪……一个多么传统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观照、想象和读解。如果说这种经典的体认模式在20世纪遭到了女性主义及随着对启蒙运动的宏伟叙事和二元思维的质疑而来的多种现代与后现代思潮的迎头痛击(想想昆德拉笔下的萨宾那与特利莎),那么19世纪的爱略特却还在这种古老的构架中重复和延续着男人们的道德拷问和判断。监牢中倔强而高傲地沉默着的海蒂,在黛娜眩目的道德圣火的烛照下委地无形,她终于承认自己有罪,心甘情愿地去服刑。此后全书的其余人物均在罪恶得到惩罚、灵魂获得拯救的皆大欢喜中慢慢修复自己受伤(因海蒂而受伤?!)的心灵和被打扰的生活。英国乡村生活特有的宁静、祥和在此出现。就是那个真正“始乱终弃”的罪人亚瑟少爷——庄园的承继人——也在自我惩罚(即离家八年)中获得谅解。当亚瑟回到家乡接受众人的赦免并真正承担起慈善的庄园主的义务时,海蒂在流放中死去。亲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期待中的现实。其实海蒂在改判流放时就已经死了,因为其后的若干章节再没有出现她的影子,就像一个不详的“祸水”,众人避之不及。
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畸形的宗教律令和道德规范令我们今人惊诧莫名。海蒂不得已的、绝望中的杀婴(试想她生下孩子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况且她并没有杀他,只是扔在路边,希望有人抱走)暂且不表,众人真正畏惧和痛惜的……是海蒂不顾自己一个寄人篱下的、挤牛奶姑娘的天然身份,却胆敢不知好歹、搔首弄姿地去攀附什么少爷!想想爱略特笔下那些备受赞赏的善良人物吧,即使没有最终的“恶果”,他们也会在道德上宣判海蒂死刑的。因为唯有此,他们才算奉行了上帝之旨,才能解除海蒂带给他们的不安与痛苦。我们今人无法理解,海蒂爱上一个身份高于自己的人何罪之有?(何况是被诱!)难道她没有权利憧憬过好一点的生活,穿漂亮一点的衣裳?难道她不能有自己哪怕高不可攀的梦想乃至幻想?!难道女人只有像黛娜那样用灵魂扼杀自己的肉体欲望才算是道德的吗?况且黛娜最终儿女成群、幸福安康,海蒂却孤独地死去!这是爱略特基督教版的因果报应,还是别有深意的消解和反讽?可怜无辜的海蒂,爱略特给她扣上“人性恶”的可怕名头,把她说成是虚荣、自私和浅薄的牺牲品,我却要说她是维多利亚时代可怕残忍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可悲受害者。这种道德规范如此深入人心,越是底层的人越相信阶级身份之天经地义、不可逾越。亚当·贝德在看到海蒂与亚瑟私会后的本能反应,多想鲁贵对四凤的“谆谆教诲”啊。而在为海蒂设置的绞刑台下,黛娜的形象多么苍白虚伪,她的抚慰既是一种阴谋——廉价的眼泪和祈祷使社会良心从此安然入睡;也是一味毒剂,海蒂在其后被麻醉的悔罪生涯中可曾有片刻惊醒,为自己啼血喊冤?
写到这儿,我忽然发现玛丽·安·埃文斯在那儿微笑。兴许她早估计到了甚至期待着有人对爱略特的叙事口吻和道德倾向表示愤激?她设置了一个圈套么?也许,爱略特没有错,“他”是个男人,“他”在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言;而埃文斯只不过借助爱略特为我们提供了19世纪中叶英国普遍社会意识和道德状况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案例。否则,在小说的叙事行文中,为理性所掌控的道德预言性(爱略特),怎么敌不过一个作家发自内心且无法掩饰的敏锐直觉与情感取向(埃文斯)?
读读那段貌似冷静、无动于衷的叙述吧。海蒂身怀八甲离家出走寻亚瑟不归,归途中又累又饿又绝望,想死不敢,想活不能,一个那么漂亮,生命如阳光般灿烂的海蒂至此已形容枯槁,灵魂与肉体均弃她而去。那双直勾勾瞪视人类的空洞茫然的大眼,比一切的虚文矫饰、铺词排句更直接地映照出一个被社会诅咒却得不到任何同情的女性令人心酸的形象。埃文斯在全书最关键的地方隐埋了天机又泄露了天机。埃文斯与爱略特,作者与叙述人,就这样吊诡地纠缠在一起。那么埃文斯是何许人?她是个为自己的性别,为自己“病态的博学多识”(斯宾塞语),为自己宗教性的献身事业的狂热欲望不断与腐朽保守的传统社会进行斗争并经常有惊世骇俗举动的学者和作家;爱略特则不仅是埃文斯虚拟的叙述者,也是她与社会周旋中不得已的绝妙伪装,这使她既能以男性作家身份被社会接受,又可以借用男性的口吻纵横驰骋,反讽地直指男权中心社会的内核;而且能巧妙地将自我纳入审视的视野,不用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是其自传体小说;《亚当·贝德》里的黛娜和海蒂何尝不是埃文斯的两个极端自我?黛娜是埃文斯年轻时倾情宗教的缩影(读读《米德尔马契》的开头),在写本书时她早已令人惊异(尤其是其父亲)地成为了无神论者,对早期的宗教狂热有着清醒的反思和质疑;海蒂则多少是她当时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与著名评论家亨利·刘易斯的同居事件被社会所不齿和排斥而产生的道德焦虑的表现,她之所以要把海蒂打入十八层地域万劫不复,或许也是对自我的“罪恶感”的一种复杂乃至矛盾的态度吧。
正是埃文斯在写作中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和道德焦虑,其作品的理性力量和观念化成分给了时人男性小说的口实,而伍尔芙则由此对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感到不满。因为“她们表现出她最糟糕的东西,导致她陷入困境,使她自我意识太强,好说教,偶尔还很粗俗。”(《乔治·爱略特》)比照《亚当·贝德》,伍尔芙的话只对了一半:黛娜确实苍白可厌,而喜欢戴首饰,穿漂亮衣衫,有着粉红圆脸人见人爱的海蒂,当她从不切实际的幻想高空划然坠落时却永远定格了自己的形象,那双直勾勾的空洞大眼在向后人诉说什么呢?
来源:《书城》2000年12期 君虹
文章末尾固定信息

